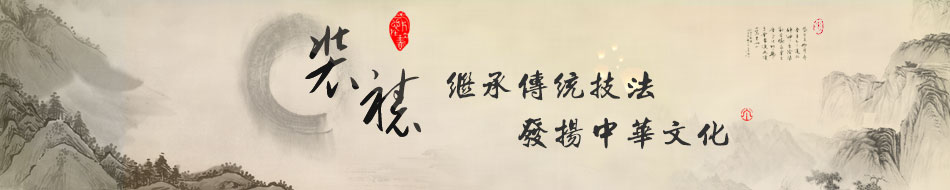2、在鹏翔字画装裱培训工艺“修复古旧书画”的过程中,一定要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,尽可能地保留原来的装潢形制,切不可画蛇添足,改变原貌。尤其在修复时要特别注意原件上的印鉴、题识,哪怕是一点点墨迹,都不能随意处理掉,力求使这些鉴定中的重要佐证不被销毁、湮灭。
3、在揭裱修复过程中,有时会发现一些被原装裱掩盖着的重要证据。如辽宁省博物馆所藏《野墅平林》四条屏,过去被奥地利人托氏定为荷兰人格洛特所作,后来经过北京二友山房装裱时,才发现画的背面角绢与托纸处有“利玛恭”字,其余字模糊不清。因此,根据各种资料判断,定为利玛窦所绘。
4、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,但后来在一幅题有松竹斋签条的寿屏上,发现其签下面还有一张被掩盖着的荣宝斋签条,由此推断,荣宝斋曾与松竹斋并存过。
5、在菏泽装裱培训过程中,要注意裱件上经裱易失的墨迹,就会获得一些宝贵的鉴定佐证。在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塔中发现的经卷,有刻经、写经及一些装裱精美的经扉画,还有少数折装袖珍本佛经,都装裱得富丽堂皇。这是我们研究辽宋时期政治经济、民俗信仰、印刷工艺的重要依据。
6、在鹏翔学习装裱过程中,对作品上的一点一撇都不可疏忽,应小心谨慎地保存下来。因为有些残破经卷长达数丈,且又糟朽酥脆,在抢修过程中不可丢失一字半字,否则,将会造成重大损失。
7、比如说,《波罗多蜜经》第七十六卷的天头纸已糜烂糟朽得难以触摸,几乎不可收拾,如不是万分小心,很有可能被破坏。但我们设法将经卷放于水中展平,然后装裱。在这张若接若断的碎片上,我们发现了一个“荒”字。它是在这块包首纸的外表,不能以整纸托连起来,所以我们就用较大的工时,把它补缀完整,使“荒”字永久在原位置上保留下来。因为,仅此一字就可以证明千年前的我国北方,不仅有“契丹藏”的雕印活动,同时还有寺院或私家抄写大藏经活动。
8、“荒”字是梁朝周嗣兴撰的《千字文》中的一个字。过去刻藏经,都是每帙或每函一字。自《千字文》的“天”字至“英”字,共480个字,历代刻、写藏经,相沿不变。由此不难看出,对一件文物来说,丢失一字与保留一字的巨大差别。
9、在修复过程中,无论是卷轴装还是条幅装,于粘地杆处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发现。还以此卷为例,当取下粘在卷尾的地杆后,发现在尾纸上署有“前朔州节度衙推士口殷勘”的笔记。因为这些字样是粘裹在地杆的尾纸上,不取下地杆是看不到的,且又是千年前的字迹,不管我们暂时能不能理解其意,都应该作为一个新发现设法保留下来,供研究者参考。
10、曹州裱画培训师们曾修一幅高二丈三尺、宽一尺六寸的绫本立幅,其本为菱形图纹,与唐墓出土的《女娲图》质地相似。此幅是以夫妇俩的生平为题材,以男者从戎、战功、晋升和女者礼佛等活动为主线,画面宏大而有气魄。画面设色鲜艳,但用笔略显稚拙,显然是民间或少数民族地区画工所为。但不愧为一件内容丰富、构图奇特的巨制,很有研究价值。可惜无名款,也无榜题,初观其质地还以为是久远之物。此帧以较粗的荆条为地杆,不是粘连而是以线缝裹,待将地杆打开后,于左下角的边缘处,有一圆形印④署记,另两字模糊不清,“清纪”二字是用墨写的,另两字的痕迹都是以朱砂为之。尽管如此,这个发现应视为对此幅作品断代的一个重要根据,而这个署记,是写在左下角,折起来的,如不精心,就会疏忽这几个字的存在,以至造成很大的损失。
11、凡修复古旧书画,一定要注意采取必要的措施,使边缘部的一些记载或某些随意题记的文字都完整地保留下来。在应县塔中发现的三幅彩色漏印《南无释迦牟尼佛像》,其中有一幅的背面边缘处就书写着“王羽家造” “日利二分”等字样,尽管有的字意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考证,但后来将其裱上了托纸,致其被掩盖起来,实为遗憾。类似这类曹州学习裱画作品,不宜托裱,采取两面加护的收藏方法有助于后人考察作品的全貌。有时在拆下古画的天地杆时,会发现在木杆上写着字迹,如“××斋装”“嘉靖×年装”或其他年号,甚至记有装潢者姓氏。诸如这些本属装潢者之戏笔,对现在的鉴定者来说,不能不说是断定作品年代的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。可是,装潢者多不注意,往往就把这些有意义的“戏笔”抛之湮灭了。